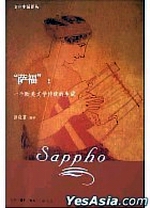 坊间有本新书,叫作《“萨福”: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。依我之见,这位古希腊女诗人身后二千五百多年间,人们对于其人其诗,不是做加法,就是做减法。具体说来,前一方
坊间有本新书,叫作《“萨福”: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。依我之见,这位古希腊女诗人身后二千五百多年间,人们对于其人其诗,不是做加法,就是做减法。具体说来,前一方
萨福生平很多说法出自后人之口,譬如她相貌丑陋,行为不检,同性恋,最终殉情自杀,等等?由此附会出不少文学和艺术作品。就中如查理斯-奥古斯特・孟根所画《萨福》,玛格丽特・尤瑟纳尔所写《萨福或自杀》,皆为动人心魄之作。然而有如学识渊博的女作家所声明的:“萨福的奇遇与希腊相关,是由于完全捏造的一种传说,即这位女诗人为一个无情的美男子自杀了,但是这个演杂技的萨福,却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娱乐圈。”(《火・序言》)以上有关萨福种种传闻,经过现代学者考证,均属虚妄。可是剥离了这些内容,我们也就所知不多了。当然,约定俗成,“萨福”或许仍被视为某种身份的代表;只是相关的道德判断,与从前已经两样罢了。
柏拉图曾称萨福为“第十位缪斯”;当时又有一种说法,以荷马为“诗人”,以她为“女诗人”,大概都是实事。那么在此范围之内,也许可以体会真实的萨福了。可是她的作品,却又散失殆尽――据说系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所焚毁,本书则云:“现代学者认为,这不过是关于萨福的又一个浪漫神话而已。”不管怎样,接下来即如知堂翁所说:“圣人们的卫道工作是完成了,可是苦了后世的文人学子,他们想一看古人遗诗的都大感困难,只好像那拣破纸的人似的,去从古来的字典文法,注疏笔记中去找,抄出里边偶尔引用因而保存下来的一行半句,收拾烬余,作辑逸的工作,现在的萨波(按即萨福)遗诗集便是一例,就是这样编集成功的。近时又有人在埃及发掘,于木乃伊的棺中得到许多废纸,中间找出好些抄本的诗文,萨波的诗于是又增加了不少,不过都是前后断烂残缺,经了专门的订补,这才可以通读,至于与原本究竟异同如何,那是无法知道的了。”(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・关于萨波》)“订补”之举诚属不得不为,然而正如海恩斯所提醒的:“有许多断片必须拼凑连合,用了不大可靠的猜想去求出它的意义来。我们不但须得解说萨波的梦,在许多地方我们却常被诱引或者至于被强迫去自己做梦,这是一个颇多危险的冒险事情,不是可以容易做得的。”
本书更补充说:“我们不要以为,我们现在看到的萨福遗诗,一定是萨福自己写下来的。萨福生活的时代,是一个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换年代。萨福的歌诗从一开始就是唱出来的,是依靠口头记诵而流传下来的。……萨福本人的声音,已经永远消失了。我们听到的,不过是层层叠叠的转述,是多重意义上的‘翻译’。”这么一来,那些断编残简,似乎也该属于“萨福”了,――虽然“萨福”的用法,已与编译者的原意有所出入。假如将萨福限定为女诗人自己,便只剩下一个名字,我们也就无话可说。那么不妨宽容一些,还是把这些抒情短诗归诸萨福名下,就像“史诗”归于荷马,“寓言”归于伊索一样。
《“萨福”: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有番话讲得不错:“‘萨福’是一个早就不再属于萨福的名字和符号。‘萨福’和萨福的诗,没有什么关系。”作为读者,兴趣原本不在前者,而在后者――就这一题目而言,我希望遇到的是“萨福”背后的萨福;至于“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”,暂且不去管它好了。而本书正可看作一部比较完整的萨福诗集,尽管诗作系由英文转译。附带说一句,类似书籍,先前有罗洛同样译自英文的《萨福抒情诗集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),更早则有署名周遐寿的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(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出版)――此书虽是根据阿瑟・韦格耳所著传记编译而成,却包含了从古希腊文和英文翻译的两种萨福诗集。
然而我们如何从这多半仅为只言片语之中看见萨福,而非“萨福”呢。本书编译者也说:“值得注意的是,围绕萨福编织出来的神话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她的残诗的解读。”读者很难不去设想:这些诗到底是写给谁的,写这些诗的到底是怎样的人。而这极有可能把我们从素昧平生的萨福引向早已熟识的“萨福”。编译者说:“如果没有萨福的诗,‘萨福’也就根本不会存在。”但是“萨福”可能反过来试图支配这些诗作,尤其因为它们残缺不全。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做到适可而止;或者借用埃科的话,能否“诠释”而非“过度诠释”。当然为了避免“过度诠释”,所实现的可能只是“部分诠释”;不过阅读萨福遗作,恐怕也只好这样了。
韦格耳说:“罗马诗人诃拉帖乌思(按即贺拉斯)曾经称她为‘男性的萨波’,这是真实的,可是雅典柰阿思给她的形容词说是一个‘纯粹的女人’,却更为真实,因为在她的诗里存着一种弥漫的女性……”可以借来形容我读萨福的感受:一个女人在真实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,如此而已。记得吉尔伯特・默雷在《古希腊文学史》中批评道:“平心而论,她的爱情诗涉及范围虽然狭隘,但表达思慕之情的辞句艳丽无比,这种思慕之情过于热切,不免带一点感伤情调;同时情真意切,用不着隐喻和引人遐想的词藻。”对于将萨福与荷马相提并论,默雷也表示不能认同。然而如果把人的内心世界看作与外部世界一般深远广大,那么正不妨说萨福是另一位荷马――这也就是贺拉斯称颂她有男子气概的原因所在。萨福对于心灵幽秘与微妙之处的揭示,有如韦格耳所说:“到末了,萨波总是回到她的音乐与她的话里去,凭了这些她将心里回环不绝的悲哀倾倒出来,这样乃使得本是速朽的东西变成不朽了。在她五百多年以后,诃拉帖乌思说,‘这埃阿利亚女子放进她的弦上去的,爱仍是呼吸着,火焰仍是燃烧着。’希腊诗选中一个名叫亚女妥思的人说,‘她的语句是不死的。’”后来所有女诗人的作品,在我看来都像是对萨福的变奏;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莫过于阿赫玛托娃了。我读萨福,每每联想到她;觉得她是努力把萨福诗作亡佚的部分逐一补全。如果说阿赫玛托娃更强调萨福委婉幽怨的一面的话,那么另外一位看来与她毫不相干的女诗人西尔维亚・普拉斯,笔下也可见到萨福的影子,因为萨福本身还有强烈直率的一面。以荷马为“诗人”,萨福为“女诗人”,真是恰当极了;萨福预示了女诗人几乎全部的可能性。
本书编译者说:“惭愧,我不懂希腊文。这本书里的译文,根据的是不同的英文译本。”我在此大概应该附和一句:惭愧,我读的是译文。其实前面提到的阿赫玛托娃和普拉斯,也是一样。那么所见真是萨福,而不是“萨福”这个翻译的产物么,就像“阿赫玛托娃”和“普拉斯”似的。文学史上讲到萨福,一再叮嘱“不可翻译”,也表达了此种质疑。当然推而广之,一切诗都不可翻译,如同知堂翁所说:“我相信只有原本是诗,不但是不可译,也不可改写的。诚实的翻译只是原诗的讲解,像书房里先生讲唐诗给我们听一样,虽是述说诗意,却不是诗了。将自己的译本当作诗,以为在原诗外添了一篇佳作,那是很可笑虽然也是可恕的错误;――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,如菲孜及拉耳特的波斯诗,实在只是‘读?玛哈扬而作’罢了。因此我们的最大野心不过在述说诗意之外,想保存百一的风韵,虽然这在译述希腊诗上明知是不可能的事。”(《谈龙集・希腊的小诗》)这里根据译作讲了许多,或许不啻捕风捉影罢。
进一步说,转译文本如《“萨福”: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,似乎更要打些折扣。对此予以评估,本该是懂得古希腊原文者所为;姑且引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来作对比,――如前所述,其中原诗译文,乃是“一一校对海恩斯本的原文,用了学究的态度抄录出来”的。译者又说:“此系原诗真面目,可资参考处当不少。”一番“参考”之后,发现彼此出入不小。究其原因,可能即在转译:“诠释”复“诠释”,难免“过度诠释”了。
例如下面这首,韦格耳评为“说的那么简单,可是说的又那么多”的,周氏据希腊原文译为:“月亮下去了,还有那七簇星。这是夜半了。光阴过去,我还是独卧。”而本书译作:
月落星沉
午夜人寂
光阴自逝
而我独眠
此种译法,显然取法于周氏早年所译之“月落星沉,良夜已半,光阴自逝,而吾今独卧。”(《自己的园地・希腊女诗人》)第二句中的“人寂”,当为翻译过程中所添加;第四句中的“独眠”与“独卧”,意义也有差别。
另外一首,周氏据希腊原文译为:“长庚星呵,带回那发光的晨光所赶散的一切的,你带回绵羊,带回山羊,带回小孩到母亲那里。”从前在《希腊的小诗》中译为:
黄昏呀,你招回一切,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,
你招回绵羊,招回山羊,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。
《希腊女诗人萨波》特地注明此首“原诗二行”。本书则译作:
黄昏星
收敛起所有
被黎明驱散的――
收敛起绵羊
收敛起山羊
也收敛起孩子到母亲身旁
诗句此种排列方式,乃为译者自创,与原来样子不符。又译者特意声明:“关于诗中最关键的动词,我选择了‘收敛’,……”或可解释为诗人玄思,却太过生硬,记得韦格耳尝以“简单与坦白”概括萨福诗作特色,则此“选择”显然不似萨福之所为也。这就已经不是转译的问题了。回过头去看前引周氏所说“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”,“收敛”云云确属“创作”,但似乎谈不上“好诗”。
(《“萨福”: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》,田晓菲编译,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,19.80元)
